中华传统文化系列谈:文物中隐藏的人情世故

从前读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总会感动,书斋项脊轩在外人看来,是毫无情感的建筑空间,但若以归家几代人的人事变迁诠释它,又有新的滋味。居室本只是空间,但人在空间里产生故事,故事本身酝酿着居住者的情感,这种空间和人的情感交互,又让空间产生新的意义。
空间如此,器物也一样。就如《项脊轩志》最后一段:“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对照苏轼梦见他发妻时,想到的是“小轩窗,正梳妆”,某种意义上,器物和空间一样是基础,情感平行交杂。过去的人写诗,都是景物在前头,后头紧跟着情。见景生情,睹物生感。器物与情感,可能同样道理,两两结合,才完整得像一首诗。
拔步床与戟耳炉里的香味记忆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张典型的明晚期黄花梨拔步床。主体晚明做工,木质颜色较深的底、顶以及纱帐、软垫、挂钩等都是十九世纪后配。拔步床是普通架子床的升级版,上方有顶,床外有空间,可放置小型凳、柜及其他生活用具。床体前设置踏步,踏步上设架如屋,即有飘檐、拔步与花板等。拔步的意思是高出地面,故名拔步床。

晚明有一张卧床很有名气,谁也没见过它什么样子,因为被主人一把火给烧了。做这事情的人,是明代嘉兴的书画收藏家项元汴,他是个颇有艺术气息的富二代,也是个知名情种。项元汴年轻时常去南京游历,偶然在秦淮河畔结识了一位歌姬,缱绻数日,山盟海誓,一个非君不嫁,一个非卿不娶。不久,项元汴离开南京,这位歌姬对他依依不舍,说了很多情话。项元汴是恋爱脑,回到嘉兴家中左思右想,觉得自己遇到真爱,便耗费巨资买了一块沉香木,请当地最好的匠人做了一张工巧奢华的卧床,之后为它配上十几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古代家具多榫卯结构,可拆可装,这沉香卧床和一堆财宝软细足足装了几个大箱子,项元汴带上它们跑去南京,决定找那女子私定终身。
谁知跑去秦淮河畔找到那位歌姬后,歌姬一下子竟没认出项元汴。项元汴被晾在一边,心里很尴尬,他便换了一个说法,找人与歌姬说,自己带了一船金银财宝过来找她。果不其然,歌姬立刻换了一幅面孔,重新梳妆,准备出来迎接他。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项元汴让人把那张沉香床放在门口,又把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堆在旁边,然后指着歌姬就说:“我以为能在青楼找到有情人,不惜千金买你一笑。谁知才过去一个月,你就把我忘了,当初山盟海誓都成了笑话。别人都说青楼女子絮薄花浮,先前我还不信,如今不信也不行了。”说罢,一把火把沉香床给烧了。好几天,那条街都是沉香气味,绕街三日,余香不绝。这条街从此得名沉香街,就是如今南京夫子庙秦淮河南岸的钞库街。

前几年,在广东崇正秋拍见过一件明晚期“朴庵家藏”款出戟耳炉。朴庵,就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后人多熟知他和董小宛的情事。那些故事被记录在冒公子于董姬死后写的回忆录文体《影梅庵忆语》里。在冒襄回忆录里,他和同是教坊司歌姬出身的董小宛一起品香,“大小数宣炉,宿火常热,热香间有梅英半舒,荷鹅梨蜜脾之气,静参鼻观”,香味的记忆在项元汴那里代表了寡情薄意,但在冒襄记忆里却与爱情难舍难分,以至美人死后,冒襄再不曾在水绘园燃起过去的热香。如果那个戟耳炉真是他们用过的,倒真有些“旧事与日远,秋花仍旧香”的意思。
带钩、铜镜与印章里的长毋相忘
有件精致小巧的银带钩,出土于西汉江都王刘非的第十二号陪葬墓。它的主人是刘非的妃子淳于婴儿。婴儿这个称呼很奇怪,在江都王那里,是称呼心上人的亲密昵称。这器物虽小,却见证了汉代贵族丰富多彩的感情生活。
这枚小带钩的作用类似现代人的皮带扣。带钩为西汉常见的琵琶形钩体,模铸,形体精小。钩首为长吻翘鼻的龙首,突鼓眼,双耳向后矜立,其后钩颈曲渐宽连接着肥鼓的钩身。钩背腹凸出一个圆形的钩钮,以钮柱连接钩腹部。整器以中剖线为轴,自钩首龙耳下开始两侧错饰云气纹,钮面亦做同心圆的错银纹样。大概是因为错入银片的银质中含金的缘故,器表装饰利用了色差烘托出需要突出的纹样来。

这枚小带钩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其既能沿中轴对半将一钩分为大小均等的二钩,亦可以利用钩首、尾两端处突出的柳钉符合成一钩,尤其是可分合的钩身内面有“长毋相忘”四字吉语,一侧钩身为阳文、另一侧钩身为阴文。两钩扣合,文字便隠匿不见,又因两钩合并成一钩使用时,将钩纽扣入革带的细槽内卡紧,整器便密不可分了。长毋相忘,是汉代人常见的词语:“你永永远远都不要忘了我”。这个词在汉瓦当和汉镜里见得也很多。汉镜里除了“长乐未央,长毋相忘”,还有诸如“君来何伤,长毋相忘”这样的铭文。如今这带钩也成相思物,入土两千多年,也将浪漫归于一抔黄土。
《太平广记》里记载过一个故事,陈朝太子舍人徐德言的妻子,才貌双绝。夫妇二人身逢战乱之际,恐怕不能相保,德言就对妻子说:“凭你的才貌,落难后也能去权贵之家,那样我们恐难相见。如果咱们的缘份还没断绝,应该有个信物。”说罢,他把一面铜镜掰断,夫妻各执一半,分别说泣言:“将来你一定要在正月十五日拿半镜到市场上叫卖,我也会在这一天去寻访你。”
陈朝灭亡后,徐德言的妻子果然去了权贵之家,非常受宠。德言颠沛流离,艰辛万苦,流亡到京城。他每到正月十五日就去市场游逛,终于看到一位卖半面铜镜的老仆,还把价钱抬得很高,别人都笑话他。德言靠着老仆找到了妻子,并拿出自己的一半镜子一对合,夫妻二人相抱而泣。徐德言最后在镜上题诗:“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这样的乱世情话,竟与汉镜上的铭文“君来何伤,长毋相忘”如出一辙。
清代诗人黎简与妻子梁雪伉俪情深,妻子去世时,他铸一枚“长毋相忘”铜印系在妻子手臂上。黎简有一首《二月十三夜梦于邕江上》:“一度花时两梦之,一回无语一相思。相思坟上种红豆,豆熟打坟知不知?”小序里说,在他的妻子死后两年的二月十三日夜,诗人梦见自己在邕江上,恰有朋友回乡,于是急忙写封信带给妻子,才写下“家贫出门,使卿独居”八字,便骤然梦醒,醒后顿觉哀伤,于是写悼亡诗五首,上面那个诗是最后一首。一样都是长毋相忘,时间跨越千年,情深所至,字字泣血。
竹笋石与雪浪石里的百感交集
一块仿若板砖的黑褐色奇石,正中似嵌着洁白竹笋,左侧还刻着蝇头小楷的诗句,末了署名“庭坚”,并有圆形篆体“山谷”印章戳记。这块奇石形似竹笋,其实并不怪异,它有个称谓叫震旦角石——即鹦鹉螺类的古生物化石。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鹦鹉螺化石标本,如今陈列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内。它的背后,是一群宋人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建立的交谊。

熙宁七年(1074)到元丰二年(1079),应是苏轼生命里较为得意的一段时光,这六年他离开杭州出知密州,然后转到徐州,再转湖州做太守,一路顺遂,诗人的身旁也围拢了一大批共同唱和的诗人,黄庭坚就是其中之一。熙宁五年(1072),黄庭坚被授大名府国子监教授,那会他和远在徐州的苏轼书信往来,常有唱和。苏轼喜欢他,评价这个江西人是“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可惜好景不长,元丰二年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差点死掉,好在有人求情,第二年被押往湖北黄州充团练副使。
身为苏门大弟子的黄庭坚当然也被牵累。就在苏轼被押解到黄州的那年,黄庭坚解职改官江西吉州太和县,南下路上,他经过安徽三祖山上的山谷寺,便以“山谷”为号。大约那年冬天,他又路过故乡江西修水,可能正是那时,黄庭坚获得了那块鹦鹉螺化石。心情抑郁的诗人在上面题了一首诗:“南崖新妇石,霹雳压笋出。勺水润其根,成竹知何日。”
南崖即南岩,在如今江西修水,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区。新妇石,即刚刚清理的奇石。霹雳压笋出,就是春雷下的笋尖自大地深处冒出。勺水润其根,成竹知何日,这样简单的句子在山谷的语境下,却别有暗喻,黄庭坚可能把自己比作那个笋尖,刚刚在仕途上探出头,却又总是不得重用:“石头啊石头,如果我给你中间的这根竹笋天天浇水,你会长成竹子吗?”
后来,苏轼重归政坛,没过几年宋哲宗亲政,重新启用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而这一年,支持苏轼的高太后病故,苏东坡作为守旧派人物被清理出朝堂,贬为定州知州。苏轼到定州不久,他在州衙菜园里发现一块怪石,体形浑圆,黑石中富含白脉,如雪浪翻滚,将其称为雪浪石。苏轼将雪浪石移置于书房前,并将书房题名为雪浪斋。之后,苏轼亲自为其定做了汉白玉雪浪石盆,将雪浪石立在芙蓉盆中,激水其上,观赏水波粼粼,雪浪翻滚之美态。

黄庭坚幻想中那枚期待成竹的石笋,在苏轼那里,化成了雪浪湍急的奇石。苏轼曾做《雪浪石诗》,从太行山的磅礴气势写起,紧接着写雪浪石的殊异,最后由雪浪石想到自身境遇,可以说是天马行空。他最后写道:“画师争摹雪浪势,天工不见雷斧痕。离堆四面绕江水,坐无蜀士谁与论。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园山水聊心存。”心情和黄庭坚在鹦鹉螺化石上的题诗是类似的,无奈中透着一丝不甘。
同为苏门学士的秦观,也写了一首《雪浪石》寄给了苏诗:“高斋引泉注奇石,迅若飞浪来云根。朔南修好八十载,兵法虽妙何足论。夜阑番汉人马静,想见雉堞低金盆。报罢五更人吏散,坐调一气白元存。”秦观恭喜他的老师得到了奇石,转而又说,如今我们空有志向,却无用武之地,只剩城墙上高挂的一轮明月。
一枚是竹笋,一枚是雪浪,镌刻在怪石上,象征了如梦似幻的人生,竹笋无法成竹,原本惊天骄魂的飞石,如今也只能成为闲时玩味的赏石。只不过,这两块奇石共同承载了苏门学士命运交杂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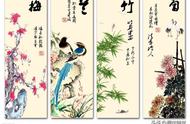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08号
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0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