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酷暑时,往往会更加向往山涧里的溪流、湖泊……任何一片水岸,总有让人感到沉静、凉爽的魔力。而与水相伴的飞蝇钓,不仅仅是“闲来垂钓碧溪上”,还需要钓者观察岸边的生命、模仿其绑制毛钩,优雅地抛投,直至钓获放流,这场与鱼的博弈,也像是和自然的一次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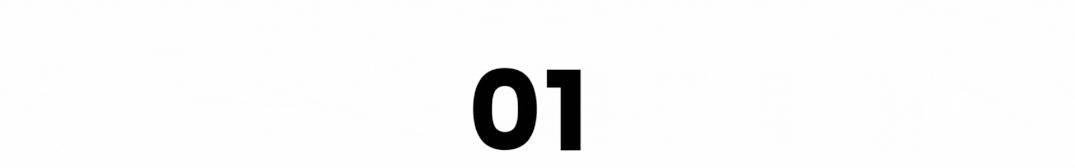
属 于 你 的 那 片 水 域
在世界上无数孕育着生命与故事的河流中,北马其顿的阿斯翠斯河(Astraeus River)与飞蝇钓有着最为悠久的交集,可以追溯至公元2世纪末。当时一位罗马作家Claudius Aelianus曾描述过,有钓者用羊毛和公鸡的羽毛扎成的假饵来诱骗鱼儿上钩,被公认为是最早用飞蝇毛钩钓鱼的记录。
历经千百年的飞蝇钓落入国人的视野,或许是从1992年的电影“大河恋(A River Runs Through It)”中的画面开始的。如果每位钓者都有一片属于自己记忆深处的水域,新疆人Inzi对鱼的兴致启蒙来自童年时离家不远的博斯腾湖,“我从小就喜欢捉鱼,也各种在野外皮。”
2012年前后,有一次他和朋友在去上海淀山湖露营的前夜碰上了一场大雨,第二天发现很多鱼因为湖水漫上了树林,也“游”进了林子,当时的景象让Inzi想起小时候抓鱼的情节,由此决定重拾这个爱好。他也坦言自己生性好动,传统的台钓方式并没有留住这位户外发烧友的内心。偶然在网上关于路亚的帖子里看到一个关于飞蝇的小板块,便一发不可收拾了。“路亚用的也是假饵,但要钓大型掠食性鱼类对技术、环境要求都比较高,而我还会享受一路骑车、露营,钓鱼是其中的过程之一,就算一无所获也很满足。”Inzi笑说自己并不是守着渔获的钓鱼者,这与飞蝇的理念不谋而合。在2015年前后,玩飞蝇钓的人少之又少。面对一些专业术语,Inzi也遇到过很多模棱两可的时刻,为此,他曾去牡丹江参加过飞蝇钓的交流会,找到了“组织”,后来又前往马来西亚考取了国际飞钓抛投的教练。“当时国内飞蝇钓在最北方和最南方发展的相对活跃,因为北方有冷水河流,鱼群种类和欧洲一些地区相似,当地有一种钓法叫‘飘蛾子’和飞蝇很像,而南方一年四季都有鱼可钓。”随之,他也把更多的时间从车轮上“挪”到了河岸边。

当我们问及“究竟该叫飞蝇(钓)还是飞钓”,Inzi说他对于Fly Fishing的理解也经历过刷新。其实两者的差异来自于对Fly的不同译法,如果将其视为一个名词——飞蝇,就凸显了大部分的假饵都是模仿小飞虫的形象;而译为动词,则侧重抛投时飞扬的鱼线和鱼竿。既然这种钓法因地制宜,飞蝇钓的风格在全球也各具特色。Inzi获得的国际飞钓抛投教练认证来自美国的一个非营利组织——FFI(Fly Fishers International),他们把飞蝇钓做了相对系统的梳理。如果从技能角度出发,有两个比较关键的环节,一是制作鱼饵,二是抛投。飞蝇钓的饵是这种钓法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自己制作而成,称为假饵(或拟饵),其主要材料往往来自鸟类或其他动物的羽毛,模拟当地岸边的昆虫或鱼类的其他天然食物,也因此这个环节又叫毛钩绑制。这可不是一节简单的手工课,“除了要了解各种绑制材料的属性,还要学会观察大自然,探索当地生态和鱼的食性,模仿蜉蝣等昆虫不同生长阶段的外形,越是逼真越能骗过鱼。此外,还要兼顾颜色的搭配、造型的美感,也会衍生出侧重于观赏性的精致毛钩。”Inzi说着向我们介绍了一本书,叫《世界上有40款毛钩》,“有些饵有特别的名字,它的造型和鱼钩都是有讲究的。对于绑制毛钩的前人工匠来说,能让一款鱼钩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在当时也算是一份殊荣。”这个过程是飞钓爱好者的“必经之路”,而和钓友们交换自己绑制的毛钩也是一种友好的交流仪式,就像球员互换球衣一样。“我就有一个盒子,专门用来装和别的钓友交换来的毛钩,这也是乐趣之一。”提及自己的珍藏,能感受到Inzi发自内心的热爱,“当然也会有小白会去买鱼钩、找鱼塘体验飞蝇,但如果玩得久了,最后还是会慢慢以贴近自然的方式去享受这件事。”正因为羽毛制成的假饵非常轻盈,飞蝇钓还需要在线和竿上下功夫,通过抛投的方式把饵送到数米甚至数十米之外的水域。“很多热衷于抛投的朋友,会把抛投时鱼线在空中的形状和距离视作自己的签名一般,不断使其趋于完美。在水面之上挥洒时的画面感是一种视觉享受,也如同一种交流方式。因为并不强调渔获,飞蝇钓的竞技性相对较弱,抛投是比较有趣的比拼环节,也能体现一个人的技术水平。”而且抛投可以在陆地上体验、练习,Inzi也经常会和朋友去草坪上比划。也正是抛投和对鱼线的控制,模仿昆虫跌落水面,并随波逐流,诠释出了这种钓法收放自如的优雅。“可能有的人在钓鱼前脑子里已经有一盘出锅的‘战利品’。”Inzi并不认可这种动机,“玩飞蝇的伙伴大多也不认同把钓到的鱼烹饪下肚。我们从绑制毛钩开始,就会把倒刺压掉,以防伤及鱼的口腔。”而且鱼也很聪明,有时它们发现这是假饵,会立马吐出鱼钩,行内人管这叫“秒吐”。Inzi饶有兴致地描述着和鱼互动、博弈的乐趣,虽然钓到鱼也很开心,但渔获并不是飞蝇钓的终极期待。“我们希望钓到的鱼回到水里之后,能像以前一样愉快地生活。”因此飞蝇钓者会尽量不用手去碰鱼。如果实在想和鱼合影,Inzi的建议是:先把手浸到与河水温度一样凉,否则对一些冷水鱼来说,手的温度太高可能会让它们表皮的黏液受到感染;而当放回时,最好选择放到水流湍急的地方,这里往往含氧量比较高,让它们吸饱氧之后再游走。整个飞蝇钓的过程像是和鱼在自然中玩一场“恶作剧游戏”,假饵、鱼竿、鱼线都是辅助互动的道具。对于环境的要求,飞蝇钓并没有太多限制,“从溪流、小河到湖泊、江、海,各类允许范围内的自然水域都可以。”Inzi说道。尽管我们看到的画面飞蝇钓者多是站在浅水中,但也不排除岸钓、船钓等方式。 Point安全提示:挥杆时要注意身边有人、或附近有电线杆的情况,尽量避免雷雨天钓鱼以防鱼竿导电及水源卫生的威胁等户外凶险因素。
“在不同的地方,需要根据实地环境作出判断、调整,比如在岸边就可以抛投;有时需要下水,顺着小溪溯流而上;如果在湖里,最好有一条船,可以在船上钓。”在Inzi看来,飞蝇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在水边认识的生物往往是其他地方的许多倍,昆虫、鸟类、涉禽......自然界的声音也很丰富。”谈及印象最深的经历,Inzi说晚上露营时蚱蜢等昆虫嘈杂的鸣叫声,简直有无数个“声部”,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有虫子正在啃食鱼竿,发出微妙的声响,而钓鱼时水面的一点点动静,对眼睛和耳朵的灵敏度都是考验和洗礼......2019年,Inzi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隐川飞蝇,见证着他从爱好者到从业者的角色转变。他说:“以前是兴趣使然, 感觉自己还不够了解飞蝇,虽然这项运动在国内至今仍算是小众,我也还在吸收更多信息,加深自己对它的认识。”而“隐川”这个名字,除了因为工作室的位置地处上海黄浦江岸的外滩,隐于川边,更寄托了他对水系周边的生命的关照,希望它们能安然地隐于川内。“世界上的很多河流仍隐匿在人们鲜有触及的地方,它们孕育着不起眼的生命,比如出生在水里又能飞于空中的蜉蝣,即便微小却能在不同的空间存活。自然界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希望人类在了解它们的同时,尽量不去打扰这种平衡,给予它们健康的生存环境。”这是Inzi无数次奔赴户外的动力,也是他作为一名飞蝇钓追随者的本心。赞比亚Chiawa Camp、Old Mondoro营地◐ 内容整理自《LOHAS乐活》,文_danz,图_受访者提供,部分来源于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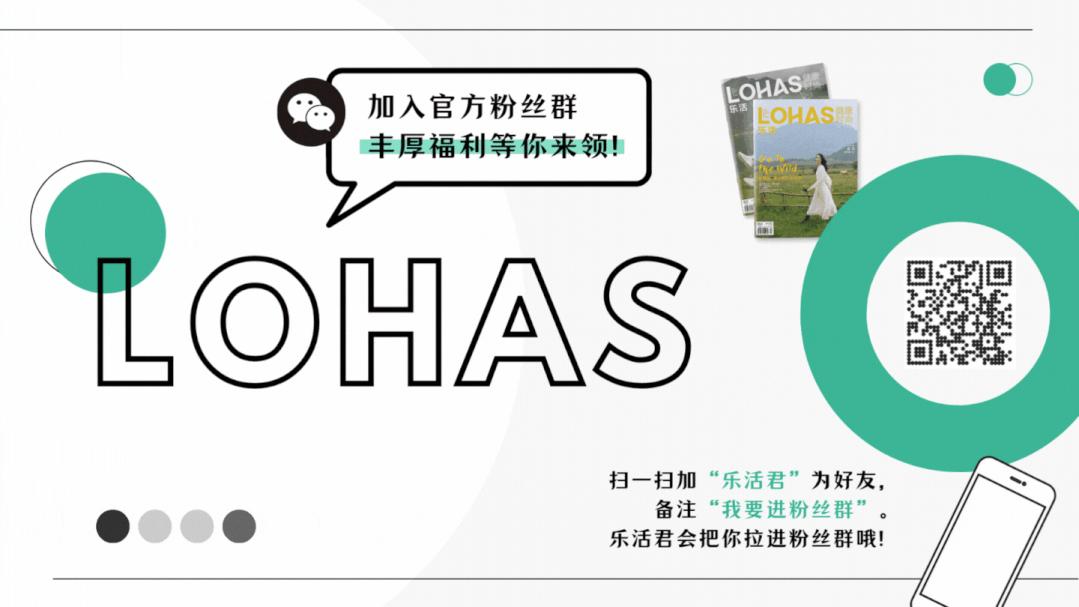
白鲟灭绝,至少我们还可以拯救濒危的它们
Tango:你有“猫病”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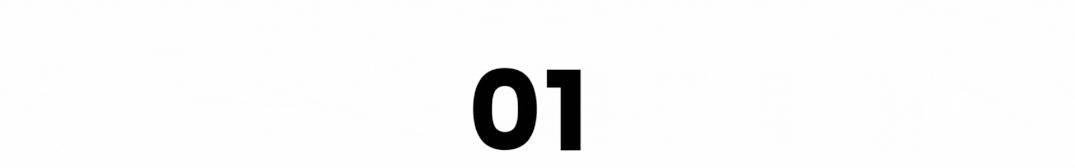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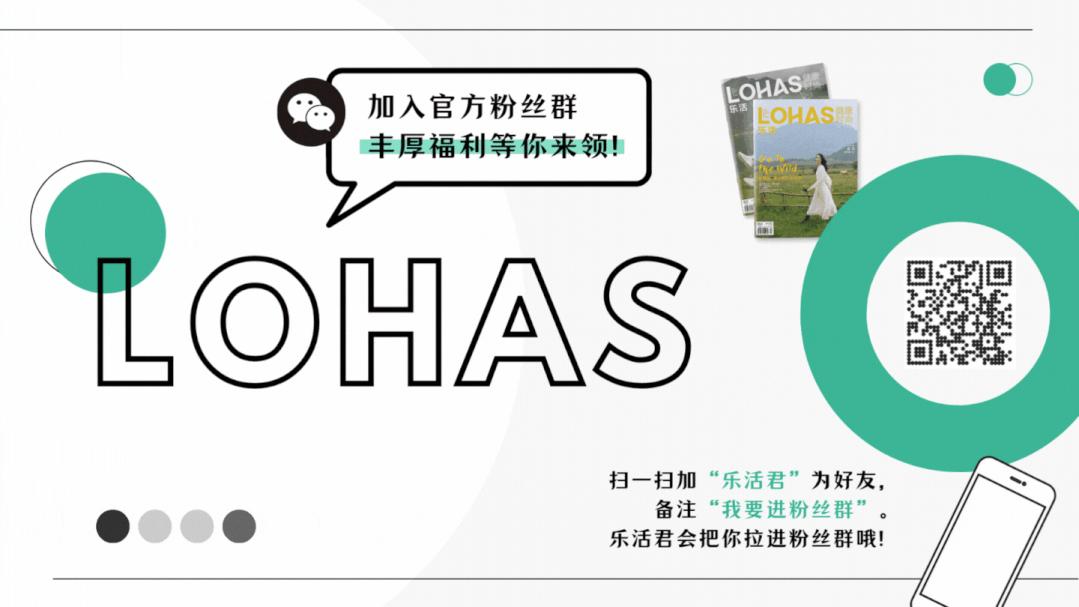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08号
鲁公网安备37020202370208号